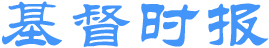一
礼仪之争这段历史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它的走向是两条线并行驰骋的。一条线是罗马教廷,一条线是康熙皇帝。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一个是要让福音落户扎根中国,一个是要借外力为皇权统治服务。但观其结果,一方面罗马教廷则宣布中国祭祖祭孔礼仪违反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让在华耶稣会的宣教士将已经开拓出的福传效果嘎然而止。一方面康熙皇帝则下旨禁教,因为传教士触碰了皇权的统治意识,使得中国对外仅仅开了一条缝隙的大门又紧紧封闭起来。就此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传教士的传教之路,被彻底隔断。不仅皇权没有得到借外力实现巩固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一些信徒也因此遇难被杀。可以说这是一段让人不忍回首的历史,无论对哪一方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悲剧。
从信仰层面而观,一切历史的走向都是由神掌控的。如果说山川河流都留有神创造的痕迹,那么历史的印痕也无疑是神留给我们的。历史的经脉与血肉虽然早已成为一个干瘪的标本,但我们身上依然流淌着从历史中因袭而来的血液。如果我们轻视或者蔑视走过的历史,不能鉴往知今,那么历史的悲剧自会重新上演。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印痕里是深藏着神的旨意和训诫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忽略了神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存在,否定了历史是由神掌控的真理。
明朝嘉靖三十一年,最先踏入中国土地传教的是耶稣会士,西班牙人沙勿略。他是从日本传教成功后进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一直踟蹰在广东一个名叫上川的荒芜小岛上,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没能踏上大陆,最后遗憾死去。中国紧闭的国门让传教士们在祷告中向神呼喊:“磐石啊,磐石,你何时开裂?”
接着,也是耶稣会士成员,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中国。他先是在澳门学习汉语,后随葡萄牙商船到广州传教,居住在肇庆天宁寺,不久又被趋回澳门。沙勿略呆板传教方式的失败,让他精明起来,他向两广总督等官员送礼赠物,什么三棱镜、自鸣钟等新奇物品,终于让傲慢的中国官员抹去冷漠露出笑脸,他被允许留居内地,并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与澳门的同工,也是意大利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住了下来,并开始建堂传教。
如果说罗明坚扣开了中国的国门,那么利玛窦却是在中国奏响了气势磅礴的传教交响乐曲的第一人。不但他的声名远播,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位传教士,并被载入中国的史册。
五年后,既万历十六年,罗明坚从澳门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抵达罗马,企图游说西方国家与中国互通使节以方便传教,但没有成功,且死于罗马。虽然罗明坚没有利玛窦那么名气冲天,但他在汉语研究方面,对中国典籍的西译,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他的《天主圣教实录》流传至今。
二
利玛窦是在1582年8月从印度的果阿州进入澳门的,与罗明坚一起学习汉语,第二年两人同赴广东肇庆建堂传教。罗明坚之后,中国教区会长便由利玛窦接续担当。十年后,既1592年起利玛窦便开启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略,以往那种僵硬呆板的传教模式,在利玛窦这里都鲜活灵动起来。
为了达到传教目的,让福音落户中国,他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在生活方式上,开始时穿的是僧服,但当发现僧人在官员面前地位低微,忙又改制儒服,在官员面前不卑不亢,并得到了官员的尊重和接纳。
他深知,若想让基督宗教在中国落户扎根,必须融合中国的主流文化,既儒家文化,将基督信仰揉进儒家观念和思想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官府的认可,才能在受阻的状态下闯出一条福传之路。他不仅穿儒服行儒礼,在举止态度、饮食习惯、坐卧起居、留胡子、坐轿子等都与中国人相同。就是将自身融入中国的风俗、礼仪和文化中,成为一个“洋式”中国人。当他所作的这些被认可后,便以送豪礼为手段,笼络结交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为他打通福传上的各种障碍。
最后一点最为重要,他一方面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产品,如自鸣钟、三棱镜等呈现在士人面前,并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如几何学、地理学、测量法等。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他的《平常问答词意》中,首次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成为中国汉语拼音的首创者。
利玛窦将儒家文化融合进基督教教义里,采取的是变通性的策略,特别突出的就是在礼仪问题上的变通。其实利玛窦在最初是禁止基督教徒从事祭祖和祭祀礼仪的,因为这里包含着叩头祭拜行为,这无疑是在膜拜偶像。不过他很快发现,中国人宁肯拒绝基督教也绝不放弃这些礼仪。在他进一步的观察中,叩头的行为也用于臣对君,孩子对父母,晚辈对长辈,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不过是一种礼节而已。他考虑到传教士在中国要立足,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基督教教义那样去执行。因此,他认为祭祖和祭祀礼仪,不过是社会性的习俗和政治性的礼节,这与拜偶像无关,所以保留和允许信徒参与祭祖和祭祀礼仪。而且把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天”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等同起来。
他这样的变通,目的是在告诉人们基督宗教与中国古代宗教是相似的,不是野蛮的外来事物。但他的目的就是要用基督宗教来一步步地同化和改造儒学,既所谓的“补儒”,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基督教化。
这一变通策略,让利玛窦等意大利耶稣会士的传教取得了很大的果效。有这么组数据可以证明。1650年(顺治七年)耶稣会教友达15万人,1667年(康熙三年)耶稣会教友达25万人,1670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信徒共27万人。
利玛窦是在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并经万历皇帝的破例准许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但是,令利玛窦没有想到和遗憾的是,恰恰因为他对祭祖与祭祀礼仪的认可和承认,成为他死后酿成“礼仪之争”的直接源头,成为耶稣会士内部及罗马教廷内部分歧的根源,更使他开拓出的福传之路前功尽弃。他一去世,在华传教士便因为对其“上帝”“天”等术语和祭孔祭祖礼仪方面,与基督教教义的融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此,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大幕,开启了一场坚守教义与变通教义的真理之辩,并成为导致在中国传教事业失败上的直接原因。
三
其实,礼仪之争在利玛窦在世的时候就已处在萌芽状态。争论的焦点与核心有两点,既有关祭祖祭孔和对天主译名的争论。这里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士大夫和儒家学者在孔庙里祭祀孔子及社会各阶层祭奠祖先的仪式,如在尸体、坟墓或牌位前烧香磕头等是否有罪?基督徒能不能参加这种活动?这些活动是否有宗教意味?
第二,术语问题,既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天”和“上帝”术语,是否就是基督教中天主的含义?这类术语里到底有没有神性意义,可否重新寻找或创造新的术语?这一问题也被称为“译名之争”。
第三,牧师为妇女洗礼能否免去那些中国习惯上认为不合适的礼节等等。
利玛窦对上述争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传教上也是这么实践的,他的传教思想和策略被称为“利玛窦规矩”。但是,在来华耶稣会成员中不是每个人都赞成利玛窦规矩的,其中以龙华民、熊三拔、庞迪我等就一直反对利玛窦规矩,内部的争辩也始终没有停止。但这只是局限在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和研究而已,处于一种探讨的状态,并没有扩大至中国信徒的日常信仰生活之中。
利玛窦死后,龙华民接掌利玛窦的中国教区会长一职,便开始全面审查和质疑利玛窦规矩,接着方济各、多明我等修会参与进来,这一争论便逐渐蔓延到不同修会,也逐渐影响波及到了一般信徒中间。于是如大潮暴涨那般,一发而不可收,并汹涌进欧洲与罗马教廷和康熙皇朝等更广泛的区域,终于掀起了一个世纪的真理之辩上的波澜,牵涉面积非常之广,涵盖了中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科技与外交等各个层面。
这个过程中,本来是一场神学上的真理之辩,却逐渐演变为现实利益之争、罗马教廷与康熙之间的神权与王权之争、文化与圣俗之争。
正如当代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所说的那样:“与耶稣会对立的有一长串的队伍,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以及世俗派传教士,如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许多拥护詹森派(17世纪荷兰天主教神学家)的人士。他们不遗余力地指出中国本土的‘上帝’这一术语和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礼仪的的确确亵渎了基督教教义。”但他最一针见血,也是最直白最真实的话是:“在双方那些忠诚、善意和虔信宗教等高尚的动机之中夹杂着嫉妒、报复和欧洲沙文主义等卑劣的态度。”这样的概括与总结,是深入事物的本质的,是耐人寻味和引人深思的。无疑,这一后果就是在真理之辩的争论过程中滋生出来的。
给人一头雾水的是,都是在“为信仰而战”的名义下进行争论的,都在剑拔弩张的时刻把自己打扮成神真理的“捍卫者”。
这种历史上经常发生而并不奇怪的现象,可以说始终笼罩在真理之上,成为基督信仰千古以来都解不开的一个谜题。人人都是保卫真理的“英雄”,都打着“神”这张漂亮耀眼的“王牌”,但人心照旧黑暗,福传事业照旧难有成效。这就是礼仪之争中的灰色地带,也正是这块灰色地带的滥觞,斩断了初露头角的福传果效。最典型的就是各修会之间明里暗里的互相争斗。
龙华民第一个在耶稣会内部挑起辩论,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第一个把论辩扩大到内陆的各修会之间,多明我会的黎玉范第一个将论辩蔓延到欧洲神学界和知识界。在欧洲,冉森派与耶稣会的激烈论争,让帕斯卡尔写出的《致外省人信札》把论辩扩展至整个欧洲。
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以“耶稣会士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为名,联合方济各会士上书教宗乌尔班八世,控告耶稣会,教宗没有答复。五年后,来华传教的多明我会士,西班牙人黎玉范因为不尊重中国文化受到冷遇而被迫离华返欧,抵达罗马后,即向教宗控告耶稣会,并提出17条指控。如对造物主的称谓、尊孔祭祖、事死如事生、妇女受洗、拜城隍、捐钱修庙、叩拜皇帝、参加教外亲友丧礼、悬挂“敬天”牌匾等等,挑起了中外之间的论辩。这个时候论辩的锋芒都指向了耶稣会,教宗英诺森十世召集枢机主教会议,支持黎玉范的控告的决定,并于1645年9月12日由罗马教廷正式向中国的教徒发出禁止称造物主为“上帝”、禁止尊孔祭祖的命令,谴责了在华耶稣会士的做法和观点。
在华耶稣会士接到这个命令大为震惊,忙派卫匡国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到罗马申辩。通过申辩,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将卫匡国的报告交给法庭(宗教裁判所)研究后,在1656年3月23日发表裁决,尊孔祭祖属中国礼仪,纯属文化活动,因此,不是拜偶像,只要不违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准许教徒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尊孔祭祖等活动。
两个决定间隔十一年,互相矛盾,彼此抵触。因此,多明我会士鲍朗高赴罗马向教廷提出质疑。结果,教宗克莱孟九世的答复是“1645年9月12日的命令仍然有效,都要依具体环境情况遵行。”
在华的耶稣会士张诚、刘英、洪若望就“祭祖与尊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问题,前去咨询康熙皇帝。这一问,让反对耶稣会的人作为口实,责备他们不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中国皇帝,实在不当。进一步引起教宗对耶稣会的反感。于是,开启了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的激烈冲突。
四
1701年,罗马教皇克雷忙十一世派特使铎罗,携教皇禁止中国教徒拜孔祭祖的敕令,率使团来华。五年后铎罗在南京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把尊孔祭祖的礼仪指为异端,违背教义,必须把这样的信徒赶出教会。
这惹恼了康熙皇帝,对他们干涉中国习俗给以痛斥,并即遣离京,由朝廷派员护送至南京。铎罗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后去广州,因拒绝交出教廷任命状,被押送澳门。澳门总督禁止铎罗活动,软禁三年。康熙的诏书还规定,凡是愿意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申请“印票”,既居留证。但只发给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其余传教士必须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康熙派耶稣会士艾若瑟等人到罗马谒见教宗,试图请教廷改变对中国礼仪的禁令,以保持正常的中外交流。教廷不但拒绝改变禁令,还颁布了一道正式通谕:凡教士都必须宣誓恪守禁令,绝对服从,否则将受到逐出教会的严惩。这一下激怒了康熙皇帝,下令将宣读通谕者逮捕。
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发布《自上主圣意》通谕,对礼仪之争作最后裁决:坚决禁止尊孔祭祖,重申1715年的通谕,凡不服从此法令者立即调回欧洲接受严惩。康熙这边将没有“居留证”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一些教士弃教从商,那些即使领有“居留证”的耶稣会士,也不像从前那样受到器重。各省的耶稣会士在行动上也受到监视,康熙对传教士的宽容政策转变为严厉的禁教政策。据传,康熙还就此将全国3000基督徒全部斩首。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便以欧洲传教士的被驱逐出境和中国基督徒的流血而画上了句号。
这场发生在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的“礼仪之争”,直接捣毁的不仅仅是利玛窦及耶稣会士呕心沥血开拓出的福传之路,也不是阻断福音落户中国的根本原因。而是让神的真理在争辩中悬空倾斜起来,偏执一隅而失去平衡,形成一种信仰上的巨大负值,导致了整个基督信仰的被颠覆被毁灭。
一场灾难的来临无论如何都不能归罪于某一个人或者一个偶然的契机,而是当所有的经验和理念在负值的层面上积聚起足够势能的时候,平衡自然就会失去,大祸也就不可避免。
至今三百多年的岁月,礼仪之争早已尘埃落定,所有的沧桑使得怀有一腔福音使命感的基督徒,不能不重新审视这场礼仪之争及其酿成百年禁教恶果的必要。圣经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这句话当烙印进我们的心灵中,否则就可能随时被狼吞噬。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