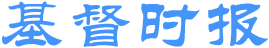编者按:《悲惨世界》是西方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两者都谈到了人类的苦难,但视角却截然不同,他们到底有何区别?本文是潘知常教授2013,05,22 在上海图书馆讲座,他的对比十分新颖,相信对读者有所启发。
潘知常,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导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社会主义学院、贵州铜仁学院客座教授。被媒体称为“生命美学创始人,爱的布道者、在全国和电视上普及美学知识的美学教父”。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生命是给予,不是取得。”
——雨果
一、那种使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
上海的读者朋友,大家好!
上海图书馆的讲座有一个系列叫做“经典重读”,我知道,过去很多著名学者专家都曾来做过讲座。最近,上海图书馆找到我,希望我也来为这个讲座系列助兴,而且,还指定了这次“经典重读”的主题:结合中国的作品重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这个邀请,我欣然应允。
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能够在上海图书馆设坛开讲,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誉,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更为看重的,那是因为,关于阅读,我也确实是有话想说,希望一吐为快。
关于阅读,我的想法,可以表达为:两个“困境”。
西方有个著名作家,在中国也很有名气,叫奥威尔,他写的一本小说,大家应该都看过,或者是起码应该都听说过,叫做《一九八四》。在《一九八四》里,奥威尔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集权社会里,所有人的思考与生活都是被指定的,后来,人们就称之为:“奥威尔困境”,在我看来,起码是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阅读中也存在这样一种困境,这就是,所有人的阅读都是被指定的,借用前面的比喻,我们同样也可以称这样一种被指定的阅读的困境为:“奥威尔困境”。
不过,随着阅读环境的根本改善,情况也在逐渐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化。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在出现新的困境。这个困境,可以借助另外一本西方的小说来打个比方,这就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各位应该也不陌生。它与《1984》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在这本小说里,赫胥黎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被指定,而是不被指定,一切皆可,后来人们就称之为:“赫胥黎困境”。同样的,在我看来,在中国,近年来在阅读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困境,这就是,所有人的阅读都是因为阅读对象的海量而成为随机与即兴的,举个例子,2005年我国出版图书的数量已经是1949年前出版的所有的书的总和:19万种,因此,借用前面的比喻,我们同样也可以称这样一种被指定的阅读的困境为:“赫胥黎困境”。
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口号:让李敖去读书,我们读李敖。我当时心里就一惊,我看到一个2006年上半年发布的一份国民阅读率调查:43.7%的中国人都说自己不读书,更不会去皓首穷经地读大部经典,因此,不能不说这个口号很有意思,它暗含的正是所谓的“赫胥黎困境”。换言之,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读什么与不读什么了,那么,怎么办呢?不如任人摆布,唯别人的马首是从,别人说什么书好,如果我也正好有空,那我就也读一下吧。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不论是落入“奥威尔困境”还是落入“赫胥黎困境”,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去阅读的经典。
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在大学的课堂上,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读书的时候,一开始,应该是“从薄到厚”,也就是说,一开始做学生的时候,并不清楚应该去读什么书,因此,正如所谓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进入大学之后,在一个合格的、称职的老师的指导下,往往是慢慢在“随便翻翻”中知道了读什么不读什么,知道了“开卷未必有益”,知道了书山书海也可能是刀山火海,于是,逐渐越读越多,但是,也逐渐阅读越少,于是,就进入了“从薄到厚”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杂乱纷纭的海量书籍里最后挑出了几十本、上百本,最终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储藏。所以,我在大学跟大学生经常这样说,我说,一个大学生应该去读什么书呢?简单而言,不论你是什么专业,不论工科理科或者文科,都应该去读人类500年前要读的书,还要去读人类500年以后还可能会读的书。各位知道,人类的书籍何其多?可是,现在只要去把人类500年前要读的书读完,把人类500年以后还可能会读的书也读完,丛数量上看,这是不是“从厚到薄”?!
我记得,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杂志——《读书》刊登了一位著名教授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很耸人听闻,光看看题目,或许会把人吓坏了:《书读完了》。作者是北大的一个老教授,金克木,他大发感叹说:我现在没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很多人乍一看,立即就会大卫困惑,人类的书籍那么多,怎么会有书读完了的时候呢?但是,仔细想想,又会会心一笑,我们的读书,难道不是不但要“好读书”而且还要“读好书”吗?普天之下,书籍确实很多,但是,好书也很多吗?所以,书是可以被读完的!
这就又要说到上海图书馆的“重读经典”了,“重读经典”,也是我们读书“从厚到薄”的一个标志。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好读书”,而且还要“读好书”。所谓“经典”,不就是“好书”吗?
不过,我又要马上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关于经典,我们往往只是见惯不惊地以为,只要师傅领进门,只要师傅指导我们去找到了经典,剩下的事情也就不值一提了——无非头悬梁锥刺股地去苦读就是。可是,积多年的读书经验,我发现,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亟待反省,也亟待解决。
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学会去准确地解读经典,经典是一,就是一,经典是二,就是二。所谓经典,就是“书中之书”。德国大哲学家尼采打过一个比方,什么叫经典?经典就像一口深井,你只要把自己的知识之桶放下去,就能够把你需要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提取出来。可是,真要如此这般,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准确地理解经典。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阅读还差得很远。近年里,我经常举误读安徒生的童话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阅读经典的过场中对于经典的误读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其实,又何止是安徒生童话,当年鲁迅先生阅读但丁的《神曲》却“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倦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最终“废书不观”。这不也说明,鲁迅先生也没有读懂这两本经典吗?难怪鲁迅先生会说:自己“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这“两个人”。以此类推,我们是否可以合乎逻辑地去猜想,事实上还有很多的西方经典,我们都还没有读懂?
第二个,检验我们是否学会了去准确地解读经典的标准,是我们是否能够去准确判别什么不是经典。这一点,对于刚刚置身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们曾经有过非常自豪的中国文化,也有过自己的经典,但是,在置身世界文明大潮之后,我们自己的经典会不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过去是经典的,现在不再是了,过去不是经典的,现在却是了?!比如,我这几年经常在各种场合举例说,有了西方文学经典这个参照系,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过去我们所推崇的所谓“四大名著”已经名不副实了,其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应该退出经典的殿堂;而过去一直被我们贬低的《金瓶梅》却应该进入四大名著的行列,应该进入经典的殿堂。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可以从两个角度着眼。一个角度,类似我们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时上语文课的角度,在阅读中,只是去看故事,顶多也就是去了解一下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人物塑造的手法、艺术特色,等等,但是,还有一个角度却不同,这个角度,是把经典当成一面镜子。在阅读中,更多的是去理解经典的眼光。例如,西方经典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眼光是什么?西方经典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眼光与我们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眼光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在座的各位读者是否已经发现?这正是在上海图书馆指定了本次的“经典重读”的主题“结合中国的作品重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之后,我之所以欣然应允的原因。
从西方的《悲惨世界》看中国的《三国》《水浒》,无疑就是阅读《悲惨世界》的第二个角度。
从西方经典回眸中国经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重温中国经典的角度。西方有一个著名的隐士梭罗,他写的《瓦尔登湖》非常著名,大家想必也全都知道。那么,在书中,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各位是否都还记得?他说,那种使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而我现在也很想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解读西方经典——例如《悲惨世界》,那么,那种使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如果我们不能够借此去准确判别在中国文学中什么不是经典,那么,那种使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
也因此,我今天的讲座的副标题,就叫做:从西方的《悲惨世界》看中国的《三国》《水浒》。
二、苦难的根源:人性原罪与社会原罪
从西方的《悲惨世界》看中国的《三国》《水浒》,我想讨论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对于苦难的看法。
《悲惨世界》讨论的是人类的苦难问题。
这当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讨论苦难问题的文学作品都有很多。苦难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而且是个无缘无故的现象,不请自来,赶也不走,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那个人可以不去面对它呢?不过,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东方特色和西方特色之间的差异,可是我们却很少去关注。当东方和西方都共同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苦难的时候,西方是怎么想的?中国又是怎么想的?更很少去关注,谁想得好,谁想得不好?也因此,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反省与反思自身的机会。
世人公认,《悲惨世界》是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换一句话说,在西方,《悲惨世界》写苦难是写得最好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坦率地说,中国文学作品也是非常喜欢去写苦难的,甚至还可以说,在数量上,中国在这个方面的作品可能还要更多。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动辄“吃不饱穿不暖”,起码是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以苦难开头。例如,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叫做:“万恶的旧社会”。可是,我们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苦难的呢?人们往往以为,在看待苦难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没有区别的,其实,这恰恰大错特错。在中国,苦难一般都被归咎于社会。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概括,可以叫做:“社会原罪”。也因此,中国人只要讲到解决苦难的方法,没有例外,就都是“改朝换代”。例如最典型的苦难作品《白毛女》,就是在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就是说,苦难的源头在于社会,铲除苦难的源头也在社会。
古代的作品也是如此。比如《三国》、《水浒》。《三国》讲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苦难,就是公元三世纪的那九十六年中的一场三国大战。开始那一年,中国有五千万人,到了结束那一年,中国就只剩下了一千五百万人。因此,不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来看,这九十六年都堪称一场旷世之乱!可是,看看《三国》的总结,你会发现,它却把这场旷世之乱总结为社会问题,答案是,只要改朝换代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曹操要改汉家的朝换汉家的代,刘备则要改曹操的朝换曹操的代,然后司马懿更是要改刘备曹操的朝换刘备曹操的代。可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以至于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万恶的旧社会”,每个朝代都贬低前面的朝代为万恶的旧社会,但是已经有二十四个朝代都过去了,我现在不得不问:究竟哪个朝代是“万恶的旧社会”?究竟哪个朝代是“幸福的新社会”。李世民上来的时候判断的旧社会的,赵匡胤上来的时候判断的旧社会,朱元璋上来的时候判断的旧社会,现在看看,都不一样。可是,如果非要今天的我们来判断,我们也只能说,都不是万恶的旧社会,但也都不是幸福的新社会。
即便是今天也还是一样,慈禧太后的时代是万恶的旧社会?1949年以前是万恶的旧社会?1949年是幸福的新社会?1978年是幸福的新社会?事实求是地说,实在也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当今之世,国民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上去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呢?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不应该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而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爱起来,让一部分人自由起来,可是,在当今之世我们看到了先爱起来、先自由起来的人的出现了吗?根本没有!现实的残酷性在于:国家崛起与国民崛起截然不同,国家崛起了,但是国民却没有崛起,结果,就只能是一场盲目的崛起,最终也只能是一蹶不振。
从这个角度去读《悲惨世界》,我们会突然发现,西方的大作家真的比我们要深刻。比如雨果,他在讨论苦难的时候就显然比我们中国人要深刻。在《悲惨世界》这部他花了三十余年的时间所精心写作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他没有把眼光集中在社会,而是集中在人性。过去我们都有个误解,以为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不会去批判了,而是会去歌颂,其实,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样的雨果就根本不是一个作家了,更遑论一个大作家,在西方,从但丁开始,莎士比亚、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毕加索一路下来,没有人例外,他们在讨论人类苦难的时候,都概莫能外地把板子打在两个字上——“失爱”。
雨果说,人类的苦难是怎么造成的?是人类彼此之间失去了关爱造成的。这意味着,雨果关注的不是社会原罪,而是人性原罪。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雨果会把自己的《悲惨世界》称做一部“宗教作品”。在中国,我们往往是把《悲惨世界》看做中国版的《白毛女》,何况,在里面还真有法国的“女白毛女”——芳汀。我们的白毛女头发变白了,法国的芳汀则是把头发卖了。按照我们中国的想法,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导致的。可是雨果根本没有这个意思,雨果在里面写了法国的地主资本家黄世仁了吗?写了法国的地主资本家黄世仁的帮凶穆仁智了吗?没有!雨果作品里的坏人德纳第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而是一个老百姓。显然,雨果关注的的是所有人的心灵黑暗。所有人彼此间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心灵黑暗。德纳第只是其中的代表。而且,主人公冉·阿让一开始不也同样是置身于心灵黑暗之中吗?
所以,对于《悲惨世界》,与其把它看做“一片面包引发的逃亡史”,毋宁把它看做“一个人的圣经”,或者毋宁把它看做“一个圣徒的诞生史”。冉·阿让所面对的苦难、芳汀所面对的苦难、珂赛特所面对的苦难,其实也都是因为失去爱以后的互相倾扎所导致的人类心灵的苦难。以冉.阿让的遭遇为例,按照中国的想法,关注的当然是他家里的贫穷,是为求生而偷了一个面包,以及因此而被判刑,然后是越狱,最后是刑期从5年加到19年。不过,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拿中国的看《白毛女》的方法去看苦难了。雨果的苦难当然不是如此,在雨果笔下,冉.阿让的苦难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结果,整个社会就成了一个相互勾心斗角相互斤斤计较的地狱。人与人之间无法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爱护来谋求生存机遇,那就只能转而借助冷漠、倾轧、仇恨和其他的种种彼此之间互相伤害的方式来为自己谋求生存空间。而恰恰就在这个社会里,类似冉.阿让这样的社会的弱者、社会的边缘人被逐渐地抛了出来。而且,即便是被抛了出来,整个社会也仍旧还是不去关注他。于是,类似冉.阿让这样的社会的弱者、社会的边缘人就不得不铤而走险,因为到最后在活和不活之间去选择的时候,他只能去抢那块面包。而这也恰恰构成了犯罪的前提。令人痛心的是,原本是他置身其间的社会以自身的不仁不义把一个原本恪守法律的一个公民逼成了一个罪犯,但是,当他抢劫以后,无情的社会又用所谓的维护正义的无情的法律来制裁他。如此一来,他当然就更不服气,他想:大家都一样,都在以各种方式去抢,难道成者就是王侯?难道败者就是贼?抢了整个国家者都没有被惩罚,难道我拿一个面包就要被判刑?这样,他当然非常不服气。于是,不服气的结果,就是社会又加重了对他的惩罚。其结果,就正如雨果所描述的:这极不公平的法律刑罚使他开始审判这个社会。他承认自己有过失, 但社会更难辞其咎。他愿意工作, 但缺少工作; 他愿意劳动, 而又缺乏面包。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19 年的监牢, 就因为一片面包, 这处罚是否又苛刻过分呢,,这种作法的结果,又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 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他认定社会对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他下定决心, 将来总有一天, 他要和它算帐。于是,他从对法律的仇恨, 发展到对社会, 对人类, 对造物主的仇恨。最后变成一种无目标、无止境、凶狠残暴的为害欲, 不问是谁, 逢人便害。他对社会的恨, 都写在了脸上, 出狱的时候, 他那样子真是凶恶可怕, 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一个善良忠厚的老实人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无比愤慨的恶魔。而且,说来很可惜, 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 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他也定了上帝的罪,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于是,他就是这样地成为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真正的罪犯。这也就是说,失爱的人性环境不但没有消灭罪,而且助长了罪。
再进一步,苦难不是来源于社会,那么,是不是来源于坏人呢?中国的文学作品最喜欢一上来就先区分好人与坏人,地主、资本家、还乡团、国民党兵、汉奸乃至日本侵略者,都是中国文学作品中频频提及的敌人。以中国的《三国》和《水浒》为例,《三国》里面的敌人是“十人帮”——三国时候的十个宦官,还有董卓、曹操,等等,三国所有苦难的理由都是因为他们而起,也都是为了消灭他们;这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坏人”。《水浒》呢?《水浒》的坏人,就是人们熟知的那“四大恶人”,他们的存在,也就是《水浒》里面的英雄好汉们动辄“排头砍去”乃至聚众造反的全部理由。可是,我们一定要问:中国的灾难真的就是所谓的“坏人”造成的?无疑,这确实是一个我们所从来没有追问过的问题,但是,这又是一个真正关键和真正真实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太喜欢写好人与坏人的故事了,也都遵奉“好人与坏人”的脸谱美学,可惜,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大凡是把文学作品写成好人与坏人的故事的,就一定不会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作品怎么写也写不过西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人从来就没有敌人与好人的区分。
何况,认真看一下中国的文学作品,就不难发现,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三国》说曹操是坏人而刘备是好人,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作为好人的刘备的所作所为真的与作为坏人的曹操有根本区别吗?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水浒传》里说“四大恶人”是坏人而水浒好汉是好人。可是我们也仔细看一看,其实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水浒好汉所干的坏事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四大恶人”,诸位不以为然?那么,请问,四大恶人直接杀过人吗?顶多也就是蓄谋杀人、借刀杀人,而且还要花钱贿赂下面的人,例如,就是连董超薛霸也要给大把的银子,但是,武松杀了多少人呢?李逵杀了多少人呢?而且根本不要花钱去贿赂,想杀就杀,一刀一个。还有,宋江抢卢俊义的时候又杀了多少人呢?小说里写得明明白白。有个水浒中人、梁山将领,他过去的职业是刽子手,本来已经见惯了杀人,可是当时一看竟然杀了这么多无辜百姓,不是也忍不住要跟宋江的手下说,赶紧告诉宋江去啊,不能再杀了。可是,我们每一个读者都知道,小说里有交代,那一次,宋江带领水浒好汉一共杀了5000多个老百姓。
所以,不能简单判断,为恶的就是坏人。自由意志的存在使得人区别于兽,但是,也疯狂于兽。自由意志是恶的根源,也是善的动力。人可以自由为恶,但是也可以自由向善。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自由为恶的可能,也有自由为善的契机。至于究竟为恶还是为善,则取决于众多的内在与外在的必然或者偶然的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同时可能是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也都同时具备人之为人的两大无限性:堕落的无限性与拯救的无限性。也因此,当某人做了好事或者做了坏事,你都不能简单判断说,做了坏事的人就是坏人,做了好事的则是好人。因为,做了好事或者坏事的,不是好人或者坏人,而都是——人。犹如做了好事的是我们自己,做了坏事的,也是我们自己。
由此出发,再来看《悲惨世界》,就会发现,雨果无疑更为高明。雨果在作品中指出: 天生的万物中, 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 不幸的是, 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悲惨世界,世界为什么会如此悲惨?在雨果看来, 正是那能够放出最大光明也能够制造最深黑暗的人心。在小说中,那个勇敢无畏地投身革命的孩子与一个浑身市井恶习的小胡同串子,其实都是一个人;那个为自己所爱者而死的爱潘妮与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把情人骗到战场上的爱潘妮,其实也是一个人;即便是那个拯救冉阿让的主教与为了拯救冉阿让而当众撒谎的主教,其实也还是一个人。
以雨果笔下的沙威为例,沙威是坏人吗?如果是中国的作家去写,那肯定就是一个坏人了,在雨果笔下,沙威却仍旧是一个人。他确实做了坏事,可是,这一切却并非出自他的品质,而是出自他的心灵的黑暗。读过《悲惨世界》的人都知道,雨果一再提示,沙威性本善良,“卑鄙”这样的字眼,与他毫无关系。雨果说,沙威的面孔没有“卑鄙的神情这一成分”。又说:“沙威虽然凶恶,但绝不下贱。”雨果还专门写道:沙威有着“淳朴、高贵的品质”。在“错误”告发了市长之后,沙威立即向他道歉,在戈尔博老屋附近,沙威发现了冉阿让,不过又无法确认,因此而心存疑虑。不去抓人,有违上级指示,难免会受到处罚;可是如果抓错了人,更有违“良心的指示”,肯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那么,沙威又为什么竟然会做了坏事呢?雨果的解释是:“黑暗的公正”,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正的程序沙威都遵守,可是所有的公正的内容沙威都不遵守。结果,沙威最终也就走上了自由为恶的道路。
过去在讲中国的《红楼梦》的美学贡献的时候,我曾经专门讲过“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以及“无罪之罪”的概念,我也特别提示过,牟宗三先生阅读《红楼梦》的体会尤为值得关注,他说,人们习惯于把其中的某些人称为“坏人”,但这些所谓“坏人”,在曹雪芹的笔下,其实都是一些“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者,都是一些 “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而绝对并非什么“坏人”。现在在《悲惨世界》中,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者,仍旧是一些 “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而绝对并非什么“坏人”。
三、苦难的拯救:爱的法庭与仇恨法庭
第二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对于苦难的拯救的看法。
前面我已经讨论过,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把苦难的源头归因于人性的原罪,这也就意味着,在雨果看来,苦难之为苦难,并非源于社会,并非源于坏人,而是源于人自身,借用《红楼梦》中的贾探春的总结,是源于人类自身的“自杀自灭”。那么,这苦难又该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拯救呢?
从《悲惨世界》,我们所看到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大体有四种。
第一种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是沦落。那也就是说,我干脆比苦难更苦难,既然苦难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伤害,那我干脆就把它化作动力,转而去加倍伤害别人。结果,在苦难制造了他之后,他又进而制造了苦难。这方面的代表,无疑就是德纳第。德纳第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在我们中国人的字典里,或许他应该属于“贫下中农”,可是,他却被黑暗变成了黑暗。这一点,在中国的以出身来定好坏的作家看来,显然无法给以合理解释。可是,这也正是西方作家雨果的过人之处。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德纳第就是如此,由于“他心里燃烧着满满一炉怨恨的火”,因此他”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甚至“仇视全人类”,当然,这也是一种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一种以不解决为解决、也以不拯救为拯救的方式,一种为雨果所完全不赞成的方式。
第二种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是革命。在《悲惨世界》里,雨果还写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雨果写的是拿破仑,但是,他的评价是“自觉的自由,一点也没有。”“战争少,屠杀多。”第二次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雨果写的是市民,对于这次的革命,雨果是肯定的,但是,也认为其实无济于事,雨果的困惑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的问号。”显然,雨果对于革命所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在这方面,各位还可以再关注一下雨果的另外一本小说,《九三年》, 雨果不到30岁就写出了《巴黎圣母院》,30年之后,写了《悲惨世界》,70岁的时候,写了《九三年》。这本小说写的是法国1793的大革命,可是,在《九三年》中,我们看不到中国作家笔下所经常出现的那种革命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比混乱的年代,议会成为擂台,法庭成为屠宰场,人与人之间成为地狱,“他们判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还有十五个月,马拉还有五个月又三个星期。” “断头台就是大革命”,这是《九三年》里的一句话。“绝不宽大,绝不宽恕”,这是《九三年》里的一个标题。结果,就像今天的化疗,革命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杀死了更多的好细胞。,因此,革命显然无法战胜罪恶。读过这本小说的都知道,雨果的看法非常明确,在革命之上,应该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第三种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是法律。据介绍,曾经,《悲惨世界》并不是叫做《悲惨世界》,而是准备叫做:《法律的命运》。因此,我要提示一下,关于法律的思考,正是《悲惨世界》的重点之所在。除了革命,世人还往往迷信于法治社会的建设,甚至以为,这是一剂根治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但是雨果说:不可能,因为,在法律之上,应该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具体来说,雨果是借助于什么来回答的呢?投河自尽的沙威。沙威的一生,可以叫做:“成也法律,败也法律”。通过他的故事,雨果告诉我们:法律无法拯救苦难!尽管人类给了法律以尊严,但是,法律本身却还有待拯救。小说写道,有一次有人跟米里哀大主教聊天,当说到审判长的时候,米里哀大主教颇有深意地反问了一句,审判长审判全世界,可是,“那位审判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 无疑,在雨果看来,在法律的法庭之外,还应该存在着信仰与爱的法庭,“最高的法律是良心”。雨果的想法是,人类社会存在两个法律,高级的法律是仁慈和爱,杜绝罪恶、唤起良知、改革社会拯救人类,非它莫属; 低级的法律是刑罚,它以为惩治是万能的,可是,其实刑罚只能加深犯罪。前者的体现者为米里哀主教,他用爱唤醒了冉·阿让,使他走上了真正的人的道路; 而后者的代表,正是沙威。要知道,上帝确实是把程序正义的审判权赐予了我们,可是,一旦我们真的误以为因此就可以借助自身去让正义得以实现,一旦我们竟然误以为自己就是正义的源头,那么,我们走上的,就只有魔鬼一途。
何况,在《悲惨世界》里,我们也通过雨果的细致描写,看到了法律的种种弊端——
首先,真正的犯罪恰恰被放过。沙威固然严酷而且精细,可是,对于真正的犯罪者,他竟然毫无察觉,而且还被利用。德纳第,法律在什么时候惩罚过他?而且,法律为什么总是让他得以成功地漏网?这恰恰说明:法律是黑暗的,也是盲目的。
其次,犯了小错却受到严厉惩罚。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只是犯了小错,但是却蒙受了法律的严惩。如此这般,法律的公正何在?法律的正义何在?而且,如此严厉的法律的不良后果,我们也有目共睹:“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却无动于衷”。“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还有,戴罪也不能立功。人们常说:戴罪立功。可是,在法律社会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比如说冉·阿让后来化名马德龙当了市长,而且贡献很大,可是法律呢?却仍旧毫不手软,仍旧要给他以严惩。这样的处罚,又如何可以使犯罪者得以被拯救?
显然,这样的法律无疑不可能成为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
第四种苦难的解决方式、拯救方式,是爱。
“让一部分人先爱起来”,以爱来面对苦难,是雨果写作《悲惨世界》时的主题思想,也是他倾尽全力希望告诉世人的警世名言。无疑,这是一种真正的拯救苦难的方式,也是我们从米里哀大主教到冉·阿让再到珂赛特的故事主线所看到的全部真缔。
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雨果发现,苦难的源头在于失爱。那么,解决苦难拯救苦难的方式呢?当然只有——爱。
在这方面,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拯救的的故事最为典型。
坦率地说,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起两部作品。一个是小说《基督山伯爵恩仇记》,在小说中,基督山伯爵一直都是疯狂的,可是最后却恍然彻悟,在结尾留给友人的信中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说:“那个人简直同撒旦无异。” 他也终于发现,快意恩仇、以暴易暴的惨痛结果,只能是使自己“像坏人一样坏”。还有一个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中的安迪也在监狱里呆了十九年,跟冉阿让一样,但是,同样是十九年,因为没有爱,冉阿让的心越变越硬,成为铁石心肠;因为有爱,安迪的心却越变越软,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
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拯救的的故事与这两部作品有关。这个被关押了十九年的男人,在46岁的时候被释放,但是,释放不等于解放,当冉?阿让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他其实还被自己心灵的囚牢关押着。也就是说,他还被关押在心灵的黑暗里,关押在心灵的仇恨里。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杀尽不平方太平”,他所发出的,也是“狰狞的笑声”。与此类似,一个越战的例子讲得很有意思:有三个美国士兵被越南人抓住了,关押期间被虐待得很惨。他们回国以后,有一次到越战纪念碑前去聚会,其中一个士兵问,你是不是已经原谅了那些当初虐待关押你的人了?第二个士兵说,我永远不会原谅。听到这句话,第三个士兵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么你就还在被他们关押着。冉?阿让也是,从表面看,冉?阿让是被监狱关押,其实,他是被自己的仇恨心灵关押。犹如中国人永远在归咎社会不公,可是却忘记了,社会不公正是被我们心灵的冷漠造成的。中国的水浒好汉也如此,看起来,宋江、武松、林冲们是上了梁山,但是他们始终还被仇恨关押着,始终都是囚犯。遗憾的是,施耐庵只看到了他们脸上刻的金印,却没有看到他们心里刻的仇恨。可是,米里哀主教却看到了,他对冉?阿让说:“如果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后对世人都怀着憎恨,那可是太可怜了,如果您能对人家都还怀着慈善、仁爱、和平之心,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高贵。”
总之,与中国的《三国》、《水浒》中所推崇的仇恨法庭不同,雨果所推崇的,是爱的法庭。而冉?阿让是那个被仇恨控制了的冉?阿让,还是重获新生的冉?阿让,也就在爱与不爱的一念之间。所以,雨果才会在《悲惨世界》中大声疾呼:“只有爱,才能消灭世界上一切不公!”
四、苦难美学的启迪: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
第三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苦难美学的启迪。
面对苦难,中国的《三国》《水浒》认为根源在社会,雨果的《悲惨世界》却认为根源在人性;中国的《三国》《水浒》认为苦难的解决方式与拯救方式是复仇,雨果的《悲惨世界》却认为苦难的解决方式与拯救方式是爱,为什么差距竟然如此之大?由此,我们就不能不进而再讨论第三个问题,这就是:西方和中国面对苦难的不同的美学态度。
显然,面对苦难,中国的《三国》《水浒》与西方雨果的《悲惨世界》形成了不同的苦难美学。
当然,正如我在前面已经一再讨论的,中国的《三国》《水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美学态度其实是不美学的,之所以也称它为“苦难美学”,主要是在“中国特色”的意义上,也是因为无论如何,它毕竟也是一种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美学实践。而中国的《三国》《水浒》的苦难美学的形成,则是因为其实它们并没有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换句话说,是因为它们虽然打着美学的旗号,但是其实在美学方面却还仍旧没有登堂入室。例如,不难看出,尽管是在从事文学创作,但是它们都还是把自己的目标与人自身的现实追求等同起来,还是在为某种现实的目标而追求、而苦恼、而表现,在它们看来,人就是人的现实性,因此中国的《三国》《水浒》的苦难美学是通过现实性来走近人,是人问、现实维度之问、忧世之问、仁爱之问,也是现实关怀之问。
这样来看,中国的《三国》《水浒》的苦难美学无非就是社会上关于苦难的的“街谈巷议”的文学化,就是民间的种种苦难故事、苦难传说、苦难经历的翻版,而且,满足的也是读者的朴素愿望,例如“冤有头债有主”,例如“快意恩仇”,例如“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例如“为富者不仁”,例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等等,不难想象,当中国的《三国》《水浒》在民间的瓦舍勾栏出现的时候,当中国的《三国》《水浒》以说书的形式在村舍街头直接呈现给老百姓的时候,是一定会因为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朴素愿望而大受欢迎的。可是,正如德国黑格尔所提醒的,熟知非真知;也正如中国人自己所发现的:“叫座”的不一定“叫好”。
而西方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苦难美学就明显不同。它是神问、信仰维度之问、忧生之问、爱之问,也是终极关怀之问。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美学方式。区别于中国的《三国》《水浒》,它是把自己的目标提高到人自身的现实性之上,是在为某种美好的理想而追求、而苦恼、而表现。在它看来,人就是人的可能性,人也就是人自己所造就的东西。因此,它不是通过现实性来走近人,而是通过可能性来走近人,也是通过可能性而获得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也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真正的人。西方的史怀哲说过: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卡夫卡在他的《随笔》里也说过:“生活意味着:处于生活的中间;用那种我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去看它。” 显然,这应该也就是西方雨果的《悲惨世界》所追求的。
通俗地说,西方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苦难美学所追求的,已经不是社会上关于苦难的的“街谈巷议”的文学化,也不再是民间的种种苦难故事、苦难传说、苦难经历的翻版,满足的更不是读者的朴素愿望,而是关于苦难的美学反思,关于民间的种种苦难故事、苦难传说、苦难经历的美学反思。打一个比方,此时的作家雨果已经并非坐在街头巷尾对社会见闻大发议论的市井百姓、大爷大妈,而是罗丹雕塑中的那个坐在地狱门口沉思的思想者,在地狱的门口,他毅然决然地坐下来思想:既然已经成为人,当然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不再是兽性?具体来说,面对苦难,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才不再是兽,才可以被称之为人?
显然,在雨果看来,关于苦难的美学思考截然区别于“街谈巷议”,俄罗斯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名作《卡拉马左夫兄弟》中说过:“尘世的许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我们被馈赠了一种神秘的感受:活生生的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上帝从另一个世界取来了种子种在尘世,培养起自己的花园,使我们得以与那个世界接触。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之根不在这里,而是在那个世界中。一旦这种情感淡了,被毁灭了,你就会淡漠地对待生活,甚至憎恨它。”(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左夫兄弟》,394页)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推崇的这样一座“自己的花园”,这座“自己的花园”是人离开自然本能走向精神世界的标志,也是自然的人被提升为精神的人的标志,也因此,面对苦难,文学作品所关注的,就不应该是“冤有头债有主、“快意恩仇”、“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为富者不仁”、“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是人类在面对苦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人类在面对苦难之际的人性表现。
这样一来,在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我们固然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三国》《水浒》中所看到的所谓苦难故事,但是,却没有看到中国的《三国》《水浒》所孜孜以求的故事性,因为,它的所谓故事其实只是为人类在面对苦难之际的所作所为、为人类在面对苦难之际的人性表现服务的。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里说:“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所卖的,当然也只是“人性”这道菜。
这也就是说,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并不是在讲一个苦难故事,而是在借助苦难故事展现人之为人的无限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与被拯救的无限性的见证。帕斯卡尔说:“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 但丁说:“人或因其功,或因其过,在行使其自由选择之时,或应受奖,或应受罚。”马尔库塞说:“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与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再看看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不能不说,与中国的《三国》、《水浒》相比较,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确实是更加美学,也更加文学,而且,也真正经典。
当然,我几乎可以立即就想象得出,很多中国的读者还是会很有些不以为然。他们会说:借助苦难故事展现人之为人的无限性又有什么用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根本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且,他们也没有改变什么。例如,他们没有没有改变芳汀的命运,没有改变德纳第的罪恶,也没有改变沙威的错误,可是,刘备诸葛亮武松李逵宋江就不同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而且也改变了生活。然而,我要强调的是,这正是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区别。文学之为文学,重要的本来就不是去记录生活,而是像上帝一样,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生活中,米里哀主教与冉?阿让确实可能不真实,而《三国》《水浒》中人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却恰恰是在文学作品中米里哀主教与冉?阿让必须存在的全部理由。打一个比方,文学作品的作用类似于大自然中的萤火虫。萤火虫,各位都很熟悉,可是,为各位所不知的是,小小的萤火虫其实比熊猫、比华南虎、东北虎都要重要。因为,它是人类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也就是说,在自然世界里,如果萤火虫没有了,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生态链条也就真的断裂了。显然,文学作品的作用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精神生态的指示物种。这也就是说,米里哀主教与冉?阿让尽管可能并不真实,但是,他们却是人类精神生态的见证,他们也在为人类的精神生存指示着方向。索洛维约夫在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曾经说:“它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年版,第213页)“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雨果的《悲惨世界》要预言的,也是“这个胜利”!
为了更加有力地说明问题,不妨顺便举一个安徒生的著名例子:
有一天,安徒生在林中散步,他发现林中长满了美丽的蘑菇,于是,他灵机一动,就设法在每一只蘑菇下边都藏了一个小礼品,然后,他带着守林人的七岁的女儿又一次来到这片林子。不难想想,当孩子在蘑菇下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意想不到的小礼品时,心中会有多么的欣喜!
安徒生的解释是:这些小礼品都是地精藏在那里的。
”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一个神父气愤之极地指责说。
安徒生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的。我可以向您担保,她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其实,这也就是文学的终极关怀的作用了,它使得所有的读者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读过文学作品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所以,综上所述,面对苦难,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关注的必须是也只能是:人类的所作所为究竟距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远,或者,究竟距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
遗憾的是,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三国》、《水浒》,我们会发现,它们表现得实在是力不从心。例如,面对苦难,我们做人要做《三国》《水浒》里的哪个人?或者,我们做人不要做《三国》《水浒》里的哪个人?由于缺乏真正的美学思考,因此中国的《三国》、《水浒》所见证的人性完全就是是非颠倒的,也是黑白混淆的。它所推崇的刘备诸葛亮武松李逵距离理想的人性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它所贬斥的曹操高俅刘禅刘璋潘金莲却果真距离理想人性非常遥远吗?实在是未必!
刘备诸葛亮武松李逵的问题,我就不去重复了,因为我在关于《三国》《水浒》的演讲中剖析过多次,各位已经非常熟悉了。曹操高俅刘禅刘璋潘金莲之类呢?他们果真距离理想人性非常遥远?很多读过《三国》的读者都说,“恨曹操骂曹操,死了曹操想曹操”,这不是恰恰说明读者对《三国》中的曹操根本恨不起来吗?至于高俅和潘金莲,《水浒》当然是想把他(她)写成反面典型的,可是,贪官高俅果真就比杀人如麻的李逵更坏吗?潘金莲为了反抗男权的压迫并追求自己的幸福,尽管最终走向了错误的道路,但是,她真的就十恶不赦吗?还有刘禅刘璋,我一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应该是充满了正能量的人物,我经常想,如果是雨果来写《三国》,他是否一定会把他们塑造成为正面人物?!当刘备挑动战乱的时候,部下都劝刘璋拼死一战,可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于是,他决定开城出降。再看刘禅,当魏兵兵临城下,刘阿斗的儿子刘谌也曾劝说父亲:“臣窃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全胜。”可是,刘阿斗根本不听,他叱斥儿子说:“汝欲令满城流血耶?” 刘备为了争夺天下,宁肯令百姓“血肉捐于草野”;魏兵为了争夺天下,不惜“令满城流血”,相比之下,刘禅刘璋的表现何等正面?可是,《三国》凭什么就偏偏要说:做人不要做这样的人呢?!
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没有让我们失望。《悲惨世界》自始至终始终是人性的无限性的见证。在德纳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昭示的是做人不能做这样的人;在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的被拯救的无限性,也是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灵魂的楷模、爱的楷模。前者是爱的源头,后者是爱的接力。
尤其是冉?阿让,雨果在他的身上更是真实地写出了人在被拯救时的艰难的人性历程。我记得,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特别强调过:“人如同其命运一样具有双重特性,即在他身上既有粗俗蠢怪又有精深聪颖;人是两个部分的交叉点,接环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两条不同的链子的同一环套。”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提示过:“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地,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诸如此类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素质,在雨果看来,是完全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的。更有意思的是,熟悉西方文学史的读者都应该知道,在西方文学史上,雨果算不上擅于心理活动的描写,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还有众多的意识流小说家,在心理活动的描写方面,都要远胜于他,甚至,有一次,雨果还公开表示过对于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不屑:“我想阅读这本书,你怎能看到40 页以上呢?”可是,在他的《悲惨世界》中,我们却看到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在这方面,各位读者都熟悉,最荡人心魄的就是他当了市长以后,为了拯救一位无辜的犯人,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与灵魂挣扎之后,毅然决然赶去自首。雨果用了很长的篇幅详尽描写了冉?阿让“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的人性挣扎,这是“自绝的关口,自救的关口” 。在他看来,“地狱正是天堂的第一种形式”,也是“人成天使的道路”,因此,只有在“直赴天国所在的深渊”里,才有真正的人性真实。
五、终极关怀,“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
以上是我关于西方的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中国的《三国》《水浒》的三点想法,在结束我这次的演讲之前,我还想再就美学的终极关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进入新百年、新千年,我已经强调过许多次:中国美学亟待完成自身的战略转型,而这个战略转型的目标,就是:终极关怀!
西方学者波兰尼说过: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可以叫做“上层知识”的东西。这个上层知识是“大作家所说和它的圣贤们所做的东西的总和”
遗憾的是,中国美学尽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在“上层知识”上也确实存在自身的重大缺憾。这就是终极关怀的匮乏,即便是在今天,中国美学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也首先应该归咎于终极关怀的始终未能被引起高度关注。迄今为止,中国美学以及中国文学之所以一直落后于世界闻名的大潮,也首先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输在了终极关怀这个美学与文学的起跑线上。
“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一千年前诗人杜牧的名言能给我们以启示。
无疑,对于终极关怀的关注,已经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
“偶尔总还得有人哪怕是单枪匹马地忽然做出榜样来,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哪怕是被扣上疯子的称号,这是为了伟大的思想不致绝迹的缘故。”
“人最终将只在教化和慈爱的功业中寻到他的快乐,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在残忍的欢娱,例如贪食、淫荡、虚饰、夸耀和互相嫉妒竞争中寻找快乐,难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吗?我深信决不是梦想,而且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
是的,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
难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吗?
我深信——
这决不是梦想!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各位!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