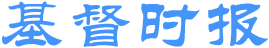去年11月11日,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国内外有不少文学界和思想界表示纪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多部深刻的作品,如《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等,可以说是比肩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布罗茨基称他写出了人类能抵达的全部深度,鲁迅将他视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日前,李正荣教授受邀通过在线讲座分享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死屋手记》的研究和思考。他的题目是:一个木制的cross的重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的残酷真实。
李正荣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等。
以下是当天讲座的内容摘要:
首先,我们进入到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二部第一章结尾的一个死亡场景:
“写到这里,我十分清晰地想起一个肺结核患者断气时的情景,他叫米哈伊洛夫。他是在我住院后的第四天死的。……现在我只记得他那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那天,寒冷而又晴朗。我记得当时阳光灿烂,一束斜晖照进我们病房那微微结着薄冰的绿色玻璃窗,倾泻在这个不幸者身上。”
“……他浑身上下就剩下一个挂着护身香囊的木制十字架和一副脚镣了。看上去他能够把他那枯瘦的脚从那副脚镣里拔出来。在他死前半小时,我们病房里的人全都安静下来,连说话都是窃窃私语,走路也几乎悄无声息。只是间或抬起头来看了眼那个行将死去的人。他胸膛里发出来的锣声越来越沙哑了,最后他用他那颤巍巍的虚弱的手摸到了胸前的护身香囊。想把它从身上扯下来,好像连这只香囊也让他感到沉重似的,使他心神不宁,压迫着他,有人替他摘下了香囊。十分钟之后,他死了,有人向看守报告,看守走进来看了死者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去报告医生。”
“……另一名囚犯注意地听了他的建议,便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他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上渐渐变僵硬了,一道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这段文字里,多次出现十字架。读到十字架,我们要暂停一下。当时作家所处的环境,东正教是他们的国教,人人都信,十字架戴在身上很正常,阅读的时候完全可以溜过它。但对于我们,可能会稍作停留,敏感一点的话,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作者写这个木制十字架、这个香囊是什么意思?这里有没有神学寓意?这是我们这次讲座的目标,我们要讨论到底它是一个写实性的客观描绘,还是有另有寓意?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和宗教及他与社会的关系。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
在苏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二流作家,当时最代表性的作家是托尔斯泰、普希金。但近100年来,他的地位逐渐升高,越来越红。尤其近50年如日中天,甚至有人说他是俄罗斯文学最高代表。近100多年来,他成为各思想阵营争取的对象。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现在每一派都想争取解读他。
在这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夺战中,基督教各流派也在争。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都在争,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东正教。东正教把他当做基督精神的宣讲人,说他的整个作品就是在讲基督精神,在讲基督教神学。几个重要的东正教神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甚至俄罗斯思想界有个悲催的观点:他们说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哲学不在俄罗斯神学著作中,而是在俄罗斯文学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的一些东正教思想确实引发重要思考。他跟那些直接从宗教角度去阐述的神学不一样。事实上,我的观点是:作为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作为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的代表。我这句话是基于当前一些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这个评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不是文学家了,而是东正教的一个什么代表。我说,这是个错误,不能局限在这里。事实上,他首先是个小说家,艺术家。他在小说和艺术中表现了他的东正教思想。如果你剥开他的文学性,直接说他的宗教性。你就找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如果你说他是用文学方式表达神学,可以;但不能干脆说他是神学、哲学。
另外,文学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语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创作于19世纪的俄罗斯,自然带有东正教这个文化语境。作品的时空、语境关系相当复杂,因此不能单一找思想。《死屋手记》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处于东正教社会中的作家,处处有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应。那个十字架,在他的书中屡屡出现,是顺着时代文化写实,还是有意识强化宗教?这要我们来做一个判断。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
大家如果要去莫斯科旅行,地铁是参观项目之一。我们看看莫斯科十号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这对于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帮助。
莫斯科地铁十号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被莫斯科人称为最阴森的地铁站。新的十号线于2010年前后建成。地铁按原来的地下宫殿原则设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的内部装潢全是黑、白、灰三色石料镶嵌出的壁画。在地铁中央大厅的一端,在拐角的墙壁上,设计师用灰色和黑色石块拼出台阶图案,艺术目标显然是吸引行人的眼睛,让行人的视线落到壁画中一个高举斧头的黑衣人身上。黑衣人被地铁艺术家用白色线条鲜明的勾画出来,高举斧子的黑衣人脚下横躺着一个白色躯体,他的前面是一个用灰白石料拼镶出来的绝望的躯体,这个直立的躯体恐怖地推出两手。阴森的壁画的确会让所有行人的意识也阴森惊恐。但是,行人们似乎也都接受这个画面,因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著名的小说《罪与罚》中最著名的场面,它是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都熟知的场面。
此外地铁站还有他的作品《白痴》的经典场面。《白痴》这部小说宗教性相当强。白痴里的男主人公,写到最后几乎是耶稣在世的形象,对世界任何一个苦难的人都充满了怜悯同情。甚至是对罪人也充满同情。最后他跟一个大坏蛋抱在一起,小说里写从他眼睛里流出的眼泪流到大坏蛋的脸上,大坏蛋从那天晚上开始也变成了白痴。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铁站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呢?这要从旁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街道说起。
1954年原名为新上帝之家街的街道被命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街道,而新上帝之家街从上帝之家街而来。什么叫上帝之家,在俄语里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婉转在于上帝之家是死亡之家。这里是专门收养孤儿、弃儿的地方,也是穷人安葬亲人的地方,或者有些异教徒不能安葬在教堂里,就葬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孤儿院和扔尸体的地方。
那为什么又叫新上帝之家呢?19世纪初,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的遗孀,罗曼诺娃,让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建一个贫民医院。莫斯科的贫民医院就建在上帝之家,因此改名新上帝之家,新上帝之家看起来辉煌了点。但是虽然外墙结构辉煌,性质还是上帝之家的性质,是给那些拿不起钱的贫民就医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在这个贫民医院做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生在医院旁边的宿舍楼。
上帝之家偏向于慈善,是被抛弃的人的接收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出生,来就医的人都是穷人。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穷人》。我想这跟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尽管他的童年可能是幸福的。他7岁的时候,父亲获得贵族称呼,10岁的时候,也就是1831年,他父亲在外省购置土地。看起来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但透过贫民医院的窗户他应该能看见俄罗斯丑陋的一面。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
他的父母对他影响很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是一个有文化的医生家庭,自然具有文化人家庭常有的温馨。在这座医院的宿舍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常给孩子们读福音书、读卡拉姆欣的《大俄国历史》。母亲玛丽亚是一位很有文艺品味的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档案文献,留下了他11岁以后写给妈妈的书信,文笔既温柔又轻柔,显然是妈妈文艺品格的遗传。但是,所有写给妈妈的信件都有一个固定的内容,就是询问“最最亲爱的妈涅尼卡”的健康。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出生,1837年母亲去世。想象一下,“最最亲爱的妈涅尼卡”的离世,对16岁的他来说一定是巨大的打击。母亲去世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到圣彼得堡求学。1839年夏天,大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接到噩耗:6月18日早晨,他的父亲死在自己的庄园。
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的死亡至今仍是一个悬案。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传统文学史和传记书描述的:作家父亲出身平民,靠自己努力转身成为贵族,再转身成地主。这位新生地主性格暴躁,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张,结果被农民打死,弃尸田垄;但是,最近几十年的传记作家宁愿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妹妹的讲述:父亲在母亲死后,内心抑郁,经常酗酒,结果在夏日夜晚,酒后失足而死;还有第三种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特别看重自己的田产,珍视自己用血汗钱所购置的土地,但是,周围的邻居很不满,为了争夺土地,其他的地主加害了这位莫斯科的医生。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愿意面对的。1839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回来。可能两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土地归了妹妹;但是更大的原因也可能是父亲死在田里。在这位伟大的作家和土地之间,隔着一具不明死因的父亲的尸体。
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然派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辞去工作,专心写作,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84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穷人》。这篇小说被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欣赏。他们认为他的作品色调灰暗,写出了圣彼得堡辉煌街道背后的贫穷和不堪入目,恰好符合时代潮流。而此时的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正想在俄罗斯文坛掀起一场“自然主义”运动。他们拿到《穷人》,如获至宝,立刻决定将其编辑到《彼得堡文集》当中,并且放到文集第一个位置刊发。涅克拉索夫说这类作品是通过钥匙孔所看见的彼得堡的生活。通过钥匙孔看到的,一定是灰色的、黑暗的、不景气的。这些作品被称为自然派。但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分道扬镳。
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
以社会文艺学来看,俄罗斯19世纪文学中的自然派是典型的进步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跟自然派走近,跟倾向于革命的作家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走近,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这个时候他倾向于进步主义。当时这个小组活动只是搞学习、宣传革命民族主义,还没到行动阶段就被沙皇发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他因为参加了这个进步小组、被抓、被判死刑。行刑时刻却戏剧般地被赦免,取消死刑,改为苦役,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服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改变,他由进步主义者变成倾向于用宗教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背景下,他写下了《死屋手记》。
了解了以上背景,接下来我们再回来讨论《死屋手记》中的神学符号。
有人说《死屋手记》是奇书,为什么这样说?他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因为只有他有这个经历,判死刑、豁免、被流放。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想写流放地很难写的这么真切。
回到书中第二部第一章结尾的故事里,有几个明显的符号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符号1:cross(十字架)
在这样一个死屋中,一个年轻的罪犯死了,在濒死的无意识中,他身上的木制的cross被扯下来,然后再被戴上。在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大背景下,在一个濒死的人身上有一个十字架,恐怕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这个特征有没有其他含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没有强化符号的含义?
这个濒死的人要扯掉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沉重还是他要丧失信仰?可能他在写实,但写实中赋予了木制十字架意义。想想看,当一个重犯脱光衣服,瘦骨嶙峋,只剩十字架和脚镣的时候……写的人和读的人大概都会有些想法。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性,这是一个极度阴森的语境中的十字架。木制的,没有颜色,挂在死刑犯身上,一切都失去了光泽,不好说是不是信仰的标志。如果是,扯下来也可能是抛弃信仰。
下面这段话我觉得他在强化死者身上十字架的神学含义。
“一个人来了,穿戴整齐,威武的样子,上前一步停下来。看着一丝不挂地只带着一个脚镣的干瘦的尸体。突然解开盔甲,摘下头盔,画了一个大十字。”
活人画大十字明显有神学含义,他这样的神学含义和已经死掉的重犯,摘下来又挂上去的十字架,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互相映衬。如果是映衬,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写实的十字架就有一定的符号意义了。
在这部作品中,死亡是自然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里面,死亡唤醒了深藏在人内心中的慈悲。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含义。因此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描写自然真实的死亡过程中出现的木制十字架的重量,与绝对时空中的人性深处的仁爱慈悲不经意间搭配在一起了。由于这种搭配,复杂的意义也就隐于当中了。
符号2:光
我们再来看这段文字:“那天寒冷而晴朗,当时阳光灿烂,一束斜晖照进我们病房那微微结着薄冰的绿色玻璃窗,阳光的一整束光,倾泻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
这一束光在《约伯记》中也可以看到。灾难来到,约伯提出问题:“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
一个受苦的人,你为何要有光赐给他,一个受苦的人,你为何给他生命?你给他生命是让他受苦吗? 面对死亡,就连约伯也会心生怀疑。
“这时死者的脸上渐渐变僵硬了,一道阳光照在……”
还是光,对于死人来说光有用吗?光的意义是什么呢?
y符号3:母亲
接下来,“有一个同样的住在病房里的囚犯。他看着军人在旁边站着,他走到军人旁边,死刑犯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话:‘他也有母亲!’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一阵刺心的痛……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又怎么会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呢?……”
是什么像刀子一样引起了“我”心中的刺痛?大家回头再看约伯记,约伯记也前后几次出现母亲,“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
约伯抱怨母亲为什么生我,他在说如果我没有生下来,就不会遭受这样的痛苦。这个小说笔下的人物说了这句话,是重复约伯的问题,还是在回答约伯的问题?
“他也有母亲!”每个人都有母亲,母亲是怜悯,慈悲的形象。我想,作者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在濒死者身上安排了个十字架,通过瘦瘦的尸体,用死亡强化符号刻写的深度,力透纸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笔记》中死亡是主旋律,但透过“cross”,透过“光”,透过“他也有母亲”这些符号,表现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慈悲。
结语
作家把死亡过程中木制十字架的重量与绝对时空中人性深处的仁爱慈悲不经意搭在一起。表面上不是特意崇尚神性,但搭配之后便让复杂的意义感隐于其中。其复杂的意义,就是东正教神学。从这一点来说,俄罗斯神学家说的还真对:“东正教的神学,不在俄罗斯神学著作里,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里。”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