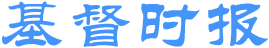吴庄是甘肃东部天水的一个普通汉人村庄,渭河冲积出来的河川地养育了全村3000多人。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普通的村庄因为几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到来而打破了他们传统的平静生活。吴庄基督徒由一个到数十人,再到数百人,从而在村庄构成、社区文化,特别是信徒的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的理念和实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来,吴庄基督教出现了一个急剧增长的现象,信徒人数从1949年的300人,在经历过20余年政治运动的“洗礼”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复兴”之后,1998年前后已增长到超过1000人[1]。基督徒群体在吴庄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区信仰群体和政治群体。
归信基督教之后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家庭观念及其组织方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家庭权威的角色界定和实施,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乃至信徒家庭与非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都要重新认识。笔者在吴庄居住的数月间充分接触并进入基督徒的个人及家庭生活,在参与观察和访谈中得以逐渐了解这些变迁。
“女圣徒”的角色
吴庄教会的信徒呈现出主要以弱势群体归信的现象,一个映证就是教会中大量女性信徒的现象[2]。这与庄孔韶在福建黄村的发现是一致的,在那里的“一个共同现象是年轻妇女基督徒数量大大超过男人数量。”吴庄教会刘长老给我提供的解释是,“姊妹们爱心好,信主后生命改变很大,又愿意传福音,和其他女人家长里短聊天的时候就把福音传开了,时间长了,当然是姊妹多了。”
李沛良(1990,237-239页)在其对华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中指出,“在许多年以来,华人社会一直是男性占优势的地位,为了维持这优势地位,男性被期待表现坚强,而不可轻易向别人诉苦。有谚语这样说:‘大丈夫宁死不屈’与‘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因为男性必须向别人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大丈夫,故努力压抑内心的感受,绝不可能随便为任何身心毛病而诉苦。……相反来说,女性在华人社会扮演被动的角色,她们被期待应该软弱和温柔,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接受‘女人是弱者’的想法……既然女人接受自己不如男人(的观点),而且自己的一生是不幸的,那么她就顺理成章地没有不承认自己的毛病或困难的理由了,总的说来,女性身心有毛病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在华人社会,女性比男性更容许把自己的毛病或困难向别人倾诉。”庄孔韶(2000,440—441页)在这个观察的基础上也指出,“考虑(到)乡村妇女闲暇时间多,而且家务可以邻里妇女凑在一起做,便造就了女人易向姐妹、邻里诉说心中琐事的机会,……或大或小的妇女同齐团体是排解女人心中积郁的良好场合。带着生活中的叹息、挫折、悲伤、怨气以及归结于命不好的心情听取宣教,终于在引人入胜的《创世记》和令人同情的《路得记》中找到答案。女人罪的羞耻以及全心全意地听从神的命令才能受恩惠的宣教,使那些有软弱传统的中国妇女获得了力量。……基督教倚重的团契活动如今刚好填补了一些妇女思想沟通场合的空缺,故今日星期聚会处中妇女团契已是最重要的力量。在团契中引证圣经、做物质与道义上的互相支持、逢时互相感化,吸引了更多的妇女入教,即团契之结合刚好是一个‘妇女倾诉过程’或‘传道与信奉过程’,也是文化传统、女性心理和宗教有机结合的过程。”
妇女的归信基督教并不等于她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事实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教会中,妇女的角色都是文化限定的。桑戴(Sanday, 1981)通过对“跨文化的标准样本”(Murdock and White, 1969)所列举的186个当代及历史上的样本后,发现有156个样本都提供了足以对性别角色的文化场景进行比较研究的资料。她指出,神圣符号并不是世俗权力角色的对应现象,相反它是决定世俗权力的首要因素。事实上,世俗权力角色乃是从神圣权力的古老观念中衍生而来。代表神圣权威的圣经教导对女性角色做了不少的界定,女性在被确认为与男性同为上帝所造因此就具有同等地位的同时[3],有更多的经文及故事透出其劣势的实际。《路得记》如果不从神超然的拯救计划的角度来阅读的话,那位顺服、温柔的路得怎么看都与中国古代故事中的才德女子的形象相近。同样,《以斯帖记》中的犹太女子以斯帖也仿佛犹太政治史上的一个牺牲品,与中国历代的“和亲”政策神似。尤其在新约以弗所书5章22-33节中特别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则要爱妻子,甚至把这提高到了“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高度,“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年出版的《主题汇析圣经》就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列出了8个方面的相关经文:亲近妻子;安慰妻子;与妻子快活度日;爱妻子;讨妻子喜悦;称赞妻子;忠于妻子;敬重妻子。相应的,就妻子对丈夫的责任也列出了6个方面的经文:亲近丈夫;爱丈夫;讨丈夫喜悦;忠于丈夫;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两相比较之下,不难发现,就妻子对丈夫的责任而言显然多了一条“顺服”。
谈到这个家庭中男女角色的问题,一位未婚男信徒用很不确定的语气说:
“家里谁说了算?应该是我吧。不过我会先问她的意见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平等,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嘛。我作头,爱她,照顾她,她呢,应该是顺服我,帮助我。唉,不过,这些是我的理想罢了,到时候如何谁知道呢?”
一位已经结婚多年的女信徒则频频摇头,感叹道这说来容易,真做起来就太难了。她说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学好怎样去顺服,经常是与丈夫口角之后,就知道自己不对,赶紧认罪祷告,但要向丈夫主动和解总是太困难,没法开口,觉得太没面子。
女信徒在家庭内的文化规定如此,在教会生活中也极为类似。哥林多前书14章34-36节这样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象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这段经文成了基督教会传统上不允许妇女讲道的直接圣经根据,尽管后来一些教派开始放松这个限定,并且还按立了少量的女牧师[4],但总的来说,妇女在教会事务上的角色是与男性不一样的。吴庄教会亦是如此,尽管也有5位女执事,但却全是妇女事工方面的,在其他方面没有一个人列为主要参与者。至于讲道则更是非常严格,妇女唯一带领聚会的时候就是礼拜三的妇女查经班,由于与会的全是妇女,带领、讲道的也是女信徒,但教会明确限定此次的讲道人不能上讲台,只能在讲台下讲。
这个女权问题在一些比较现代的大城市里的信徒中,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信徒中,显得问题比较大,“凭什么女的就要顺服男的”?一些女信徒就此提出疑问,“难道这么说来,在家庭中,男性就是要比女性优越吗?这不是与‘人人生而平等’的教导直接违背吗?”应该承认的是,这个在城市教会,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群体中颇受关注的问题,在吴庄教会几乎觉察不到,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也很少有女信徒对这个问题提出置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信徒的年龄结构,吴庄信徒的年龄普遍偏大,年轻人比较少,而这一代人中大部分还是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夫为妻纲”的想法、“三从四德”的观念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发挥作用。退休教师李长老(秦城教会)的看法可以说有一定代表性:
“丈夫在家庭里是头,这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遵守。况且,圣经说女人要顺服丈夫,但同时要丈夫爱妻子,要是丈夫对妻子不好,你想妻子也就很难顺服丈夫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地位高低的问题,而是家庭角色不同的问题,丈夫在家里需要的就是尊重,妻子最需要的是体贴和关怀。我觉得圣经将丈夫和妻子的角色这么分配非常有智慧,与男人、女人的天性正好相配。”
吴庄信徒之所以对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教导接受得比城市年轻信徒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采用了原来所熟悉的儒家观念体系来理解和阐释基督教的教导,使用了传统文化的“旧皮袋”来盛放基督教的“新酒”。这样的策略产生了3个方面的效果,首先是基督教的教导得以被信徒接受并执行。其次,反过来说,传统文化观念也借着新的信仰形式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下来,基督教成了盛放传统文化“旧酒”的“新皮袋”。其三,无论是基督教的经典教导还是地方传统文化观念,都在一些内涵和意义上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化,与原来的经典体系出现一定的偏差。吴庄信徒在接受和执行“女人要顺服丈夫”的时很少想到“教会要顺服基督”这个属灵的层面,将这个本来具有群体性的属灵意义的教导化约为简单的个人性的生活指导。同时,“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观念又被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神造世人”的教导所修正和改造,至少在理论上不再具有地位差别的政治色彩。
家庭权威的形成与转移
基督徒认为,家庭是神所设立的三大制度中的基础[5]。既然是制度,显然就有结构,有角色的分配和权威人物的出现。在吴庄,体现家庭权威的一个符号是住房的分配。在南北朝向的三间正房中,中间一间一般最宽大的,谁占有这一间正房就表明谁是家中的实际权威。这反映了民间住房平面配置上的儒家礼制理念,客厅符号所指代的是代表家庭与外界交涉,占据客厅者就等于是一个家庭的外交官,表明他具有代表整个家庭决策的权力。传统来讲,中国家庭里的权威一般是长者,在其年老时的权威主要来自道德伦理的文化规范,而不是实际的经济权力。
吴庄是一个移民社会,尽管是一个大姓村庄,但并没有形成如福建、广东一带那样的完整的宗族体系(弗里德曼,2000)。吴庄的吴姓与山东平原县后夏寨的李姓(兰林友,2002)类似,尽管是一个姓,却并不是一个来源,此吴非彼吴。吴庄的长者对这个区别还很清楚,到灵强[6]这一代就几乎没什么概念,只是隐约知道哪几家是最亲近的,哪些则更远一些。吴庄也没有严格的取名辈分规则,借村民吴召仁的话说,“我们取名字都是乱取,没那么多讲究,只要不与本家长辈同名同字就行。”1949年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强行消除各种传讲儒家宗族理念的文化形式,尤其是“扫四旧”把吴庄的川地坟墓都全部铲除推平以助规模耕种[7],在事实上禁止了传统的墓祭仪式[8]。在这样一个家族/宗族组织不完全、势力相对比较弱小的社区里,家庭权威形成及转移的经济因素就额外显著。Sung(1981,pp337)认为,家产来源不外乎两种,继承与个人创造。如果分家时继承性财产(如土地)占主导部分,那么父亲的权威就会较大,反之,如果家产是由父亲与几个儿子共同创造而来,其权威就会大大削弱。虽然由于伏叔是唯一的儿子而没有分家,但确实由于家产的创造是由他与其父亲共同创造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他创造的,家庭的权威天平显然更倾向于伏叔。因此我们就更能理解这个事实,当伏叔一家还住在老院子时,正房是属于爷爷的,而到1986年迁入现在这个院子的时候,由于当时出资出力的都主要是伏叔夫妻俩,很自然的就由这对年轻夫妻享有了正房。正房居住权的这次转移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家庭权力转换的事件,具有年轻一代接管家庭权威的象征意义[9]。
但基督徒的权威形成与转移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即与超自然的神的关系,其表现方式一方面在于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以及祷告中的“方言”恩赐,另一方面也需要信徒之间及教会的承认(这主要见于基督徒所讲的生活见证)。这种权威的来源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儒家式的伦理的,而是超自然的,其神圣性使得这个权威更加不容置疑。这种权威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最显著的就是饭前的祷告,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向神祷告的权利,但只有作为权威的家长才能以“奉主耶稣之名祷告”来宣布结束。这个“仪式”是每天重复的,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其效果是植入了每个家庭成员的血液里。每天的饭食在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的同时,还起到了提醒自己所面对的最上级的权威上帝及与家庭中的权威(通常是父亲),同时也在这样的定位中得以确认自己在神—人关系中及家庭中的角色和位置的作用。
——————————————
注释:
[1] 需要提到的是,乡村基督徒对于信徒人数的统计并不准确,也不是按照信徒个体来进行计算,而比较多的采用家户为单位来估算。
[2] 女性信徒众多是普世基督教的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归信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无论是耶稣所主动接触的那些为犹太人所撇弃的税吏、妓女及外邦人,还是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所最先得到的信徒(女人、太监等),都是当时社会中的边缘群体或等外人。
[3] 最常用作证据的经文是《创世记》1章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既然男女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男女生而平等。另外一处较常使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4] 中国三自教会里的女牧师比例与国外相比之下算是很高了,但仍然还是“少数群体”(minorities)。而且这些神职人员中担任教会主要负责人的更是了了无几,这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正好一致。可见,神圣(sacred)与世俗(profane)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界限分明,可作类比之处甚多。
[5] 三大制度分别指家庭、教会和国家。
[6] “灵强”是我的朋友,正是借着与他的私人关系,我得以进入吴庄,并住在他父亲家,我称其为“伏叔”。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以将文中涉及的人名进行了处理。
[7] 我在吴庄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见不到几所坟墓。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吴庄原来的坟墓主要就在川地里,“扫四旧”时全部铲平了,现在见到不多的坟墓都是1970年代末期以后的新坟。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坟墓埋在山地,不至于占用易于灌溉、产量高、收成能保证的川地。吴庄一带的坟墓非常简单,只是一个锥形土堆子,几乎没有立碑记录名讳及其后裔的,倒是在霍村附近看到4座水泥浇铸的坟墓,还立有墓碑。这是一个1949年逃到台湾的吴庄人前几年回来给父母和祖父母新立的,因为他在庄里已经没有别的直系亲友,无人照料坟墓,立这个墓碑是为了以后自己及子女回来看望时还能辨认。
[8] 这种早已渗入村民血液的民俗是无法长期禁止的,1980年代以后又开始了清明时节的墓祭,有些坟墓已经消失在田间地头了,村民们就照着记忆在田头点烛、焚香、化纸,以表心意。
[9] 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次的搬迁过程也是一个范杰内普(Van Gennep,1960)所谓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也经历了分离、过渡与重新整合这三个阶段。或者说是特纳(V. Turner, 1969)术语库中的结构——反结构——结构三重过程。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